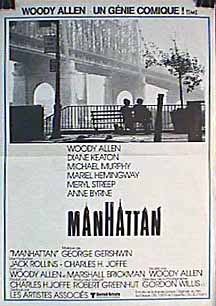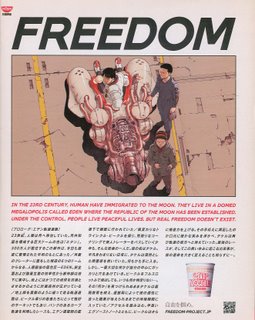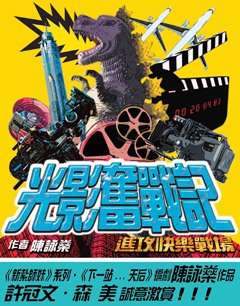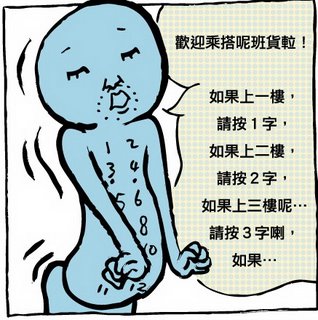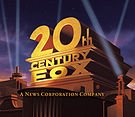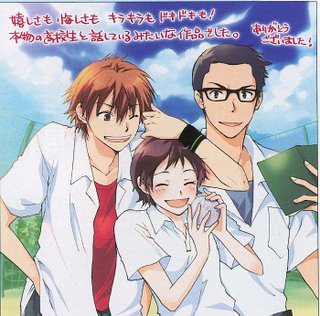半夜,因為忽然要翻查一些資料,往書櫃找其中一本最愛的書—湯禎兆的遊於日本映畫。當年很愛這書,因為當年很愛看日本電影,那時看湯的文字和影評都覺得很有味道,而且書的封面設計獨特,所以即使是學生時代,也捨得買下這本在圖書館已看過多遍的書。今晚翻著它,發現自己將它用包書膠包了起了,而且是用了「辰衝包書法」。
曾幾何時,我在辰衝當過小小的店員。在海港城老店。那是一所很別緻的店。老闆是一位姓李的老先生(相信辰衝是他的家族生意),很少話,但對下屬和書本一樣嚴謹。我有幸在那裡工作過數月,像渡過了一個秋天,學過一些辰衝的規矩,那時不覺怎樣,現在想來,那些小事都是很好的記憶。
我是店裡的小工,基本上一切低層工作也要踫。他們最不喜歡做的就是「包書」,所以經理很快教懂我辰衝包書法,從此這些重任便落在我手。辰衝包書法的大原則是愈少用膠紙愈好,還有一本書四隻角都要包得整齊貼服,不能馬虎,萬一老闆QC時發現不滿意,必被打回頭重造。
還有老闆是環保份子,店中所有用過一面的A4 紙都自動成為Cashier的Memo紙,只是我必需將一張A4紙分作均等的四份,放在一個memo格內。自少不是愛整齊的人,也不覺得隨手將一張紙分四份有何難度,偏偏李老闆就將我造的環保memo紙打回頭,說我「界」紙的邊位不是直線,相當難看。於是經理又要教我一遍,先將數張紙一起壓出深深的摺痕,然後將刀片從紙內向外「湯」開。這樣就可保證紙邊是不會突出的直線了。
問題是,要做到效果良好,一定要逐張紙「界」。將幾張紙壘起來的界的話,邊位仍是崩口的。
經理說:「老闆要求高嘛。」但這界紙法要多付出時間。可是當我見到大疊分割出來的紙都是一樣整齊如新,就明白為何他要這麼堅持了。他要我們知道,店中的一切都是給客人看到和用到的,必需以最好的表現出來。一本值一仟大元的書,和一張環保紙一樣,能表現出小店的態度。如他發現我們不小心對待書本,就會黑面,叫經理轉告正確待書的方法。
我有理由相信,李先生對小節的嚴謹,皆因他是唸建築出身的,他說那分店的室內設計出自他手筆,的而且確,去過那所舊辰衝的(現在該是LCX的一部份),都會感到那小店跟其他的分店有所不同,很有英國小書店的溫暖和學術味道。
小店全用深啡色的木書架,當中佔當眼位置的是一列新鮮出爐的Paperback,接著的是一堆洋雜誌,之後是Bargain Corner和Children's Corner。但我最愛打主意的,是店中那個小房間,是一個專賣Art Books的位置,電影、建築、油畫、舞蹈等等…那時很希望有天可以逐本逐本將膠袋拆開讀個夠。但我每天能跟它們有「親密接觸」的,只有早上數分鐘,因為經理派遣我做一項很重要的工作—每天回來第一件事,就是拿著雞毛掃,掃一片全店書架上的書,確保老闆和客人們觸摸書本時,不會感覺到上面有塵。我視這工作像小和尚每早掃落葉,工作簡單,但需專心地做。掃至Art Books Section時,我便會認一下書的名字,於是很多Artist的名字都是從那些早上記回來的。
正門的右面是付款處,也是「掌櫃的」跟一些熟客們聊天、談小說、建築、甚至文學的地方。我記得那時一位港大的退休教授,就習慣於下午的優閒時份,前來跟李老先生聊天;這時站在一旁的另一位阿叔店員會趁機打蓋睡,女經理也趁機小休吃點心去…
那時的辰衝員工,對英文書有一定認識,所以會跟客人有交流,會給意見,有時會見到他們跟客人聊上半小時研究流行小說。
那所小店其實有不少名人來過,我記憶中有鄭丹瑞、谷德昭和他那時的音樂界女友。但於我來說,最神聖的一次是…一位女客人前來,跟經理說兩句,經理拿過她的書單,執了大堆英國文學的書本,是Jane Austen那類的小說。女客人聲音低沉,我像不久前才聽過,卻記不起是誰。她離去後,經理問你知道那是誰嗎?我不知道。她說,你有看甜蜜蜜嗎?她是那編劇,剛拿了最佳編劇獎,是我們的熟客。
經理有所不知,那時我已聲稱自己很喜歡岸西,趕著追出去也來不及了吧。後來,我受不了海港城熱烈的聖誕氣氛,和週末也要上班的失落,於是轉職,當了補習老師。後來海港城大革新,那小店結束了。樂道總店成了熟客們的寄託。現在辰衝已經營網上書店了。
現在想來,書店店員的工作也許是我幹得最快活的工作。